在哲學叢林裡散步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樹林裡有兩條岔路,而我/我選了人迹罕至的一條。/一切變化由此而生。) --Robert Frost
Friday, December 22, 2006
非關集體回憶
人對他人有情,對外物亦一樣有情。我本以為沒有誰不明白這個道理的。小如一個用慣了的鑰匙扣,一個每天用來飲白開水的玻璃杯,我們固然對之有情,而大的、存在良久的如一座鐘樓,伴隨著小島的人們成長,我們對它的情,又豈會不深厚綿長呢?
偏偏這種簡單道理,被認為不能登大雅之堂。於是抗議者為迎合(當權者/傳媒)口味,得常常高舉「集體回憶」作為反對清拆的理由。對這個潮流用語,我有點疑懼。「集體回憶」於我是太龐大、太正氣凜然、太欲除去personal feeling的講法了。當然,要評價一些建築物是否值得保留時,除了訴諸其歷史價值建築特色外,它是否能勾起大部分人對某個時代之生活細節或重大社會事件的回憶,的確是個比較可以「量度」的標準(從報上得知,民政局計劃將「集體回憶」納入未來的文物評級準則中);但我總覺得,「集體回憶」只是一個堂皇的、可以用來跟別人辯論的理由,而在這堂皇後面,最讓人難以忘懷/釋懷的,根本是一些非常非常個人的東西。這些個人的東西,太微不足道了,也太私人了,無法是反對清拆的好理由,所以我們只好繼續冠冕堂皇下去,有時,會連自己也糊塗了……
我對鐘樓有情,並非因為它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小輪加價/蘇守忠絕食/唯一的過海交通公具/小輪上嘆海風看夜景/最後一天去坐船/在電視新聞上看著鐘樓被毁)之盛載體。其實那情的由來,說來很瑣碎,只不過是鐘聲所曾給予我的心靈潤澤。
十多年前,我喜歡去大會堂聽音樂會。鐘樓的鐘聲,常常在我路過大會堂一帶、正低頭思索著當時以為極其重要的事情時,冷不防的響起。清脆卻又帶餘韻的鐘聲。它有一種奇妙的力量,能將我由困擾纏結的心事中一把扯出來──就像剛從夢境中醒來時那種迷離疑幻的感覺。鐘樓近在咫尺,但鐘聲卻像來自遙遠他方,耳際迴盪著噹噹之聲,心靈會感到平安、寧靜。這時會突然覺得,自己所想所憂的,都是雪泥鴻爪,在綿綿無盡的時間長河裡,那太不起眼了,何必為此等小事而發愁?海風吹得人舒爽,鐘聲提醒我音樂會要開場了,於是邁著大步,我輕快地跑向大會堂的音樂廳……就是如此瑣碎的事情。後來雖然因為搬去了新界而少踏足中環,但偶然想到鐘樓還安好地立在維港旁邊時,就會像想起老朋友在遠方生活愉快般,感到很踏實。
此所以,從電視看到鐘樓被毁,心裡像被掏空了似的。
有很多年,我都沒法搞清楚,鐘樓在十五分、三十分、四十五分和正點的各次鐘聲,到底有什麼不同,只是偶然會奇怪,為何鐘聲所奏出的melody有時好像不完整的呢?直至今年讀到SEE雜誌列出每小時四款不同的鐘聲,才知道原來十五分鐘和四十五分鐘的melody都是以sol音作結,因此呈incomplete的聽感,而正點和三十分鐘則以do音作結,所以很有圓滿的聽感。
而圓滿與不圓滿的鐘聲,今天都消失了。
Sunday, November 12, 2006
天星
Sunday, November 05, 2006
公開的隱藏
但已有好幾年,沒有了執筆寫日記的衝動。每天腦海裡縱有很多念頭略過,但也提不起勁去紀錄下來了。生活變成了零散的碎片。常常是:昨天作好的決定,今天又重新思索起來,甚至得出全然相反的結論。好像兩個我互不相干。不再像年少時那般情緒化(希望不是變成了麻木),但卻找不到一個可以支撐的點。一個將碎片統合起來的點。
要說覺得活得不愉快嗎,也不是(世界上有太多人受著各種苦難)。但總感到疲憊。有時就只想奢侈地隨便坐著、躺著,讓腦袋安靜下來,什麼也不要做不要想。所以很佩服和羡慕那些為著某個理念而努力不懈的人,那些有支撐點的人。我常常是:帶著莫大的熱情去了解,最終卻無法投入進去。像隔著一層玻璃櫥窗在觀看,但走進店舖時卻什麼也不想買了。突然什麼興致都沒有了。
竟寫下了這些,嚇了我自己一跳。(多謝你竟然讀完以上幾段與你的生活無關痛癢的文字而仍然沒有離開)本來是因為讀了楊照的《為了詩》而想寫點什麼的。這是我第一次讀楊照的書。那一晚,心情特別不安和悶悶不樂,放工時,臨時決定要放縱一下,不回家了,隨便坐上一輛西行的巴士。車窗外英皇道的風景緩緩略過,我奢侈地坐著,什麼也不欲想。來到銅鑼灣突然決定下車,信步走到樂文。書店是給我最大快樂的地方,但那天,我卻突然什麼興致都沒有了,什麼書都不想看,直至於無意中見到楊照的書。朋友曾經讚楊照的書好看,於是我買了一本叫《為了詩》的,便走。回家的路上,讀著,突然,像遇上了一條美麗的山川般,停住了腳步,說不出一句話來。噢,相逢恨晚。
其實對於新詩,我總是帶著莫大的熱情去了解,卻始終無法投入進去。但很喜歡楊照為新詩而寫的這些文章。楊照再三強調他不是詩人,但卻不斷為新詩抱打不平,細絮說著他對詩的這樣那樣的感受。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被他對詩的熱情所深深感動。
其中一篇叫「詩是公開的隱藏」,我很喜歡。楊照講了一個故事(契訶夫的《吻》):一個士兵去參加舞會,不經意闖進一間小房間裡。在黑暗中,他被一位認錯人的女孩親吻了一下。女孩很快察覺吻錯對象並逃開了,但這個吻,卻令士兵被「包圍在神秘的力量」之中。他覺得,這是一樁生命裡很重要很偉大的經歷,但不知為何,當開口跟同伴講述這經歷,卻一下子便說完了,完全引不起同伴的興趣。
楊照說,詩,能將士兵所感受到的那個吻的秘密,以一種「公開的隱藏」的形式,書寫出來,「詩告訴人家,我這裡藏著特別的東西,我是這樣藏那樣藏,藏來藏去後你勉強可以看到這一角那一角的暗示,或模糊輪廓的外形,然而真正的是什麼,我死也不會講明。」(24頁)
我想起,自己也常常經歷那個士兵的遭遇:想把深刻的感覺說出來,但一下子便說完了。(可能因為這樣,我需要寫作,雖然寫的不是詩)
常常覺得,詩意存在於細節之中。記得幾年前,被感情事搞得很煩。一位很稔熟的老師知道了,想開解我,便帶我到西貢碼頭。午後,我們一起坐在石砌的海堤上聊天。聊著聊著,也許是海風的緣故,老師竟睡著了,頭還枕在自己的鞋子上。我不想吵醒他,只獨個自看海,感到很平靜。
第二天,我把老師帶我去西貢的事告訴了當時的伴侶。但我無法講得清楚。一下子,便說完了。我甚至沒有提到老師睡著了。
幾個星期後,這段感情走到了盡頭。欲分手的那天,伴侶竟有樣學樣,也帶我去西貢碼頭,也跟我坐在石砌的海堤上。對這種重複,我感到很荒謬。
現在回想,也許他就是不懂得「詩意存在於細節之中」。其實西貢碼頭不重要,石砌的海堤也不重要。
Tuesday, October 17, 2006
Friday, October 13, 2006
Sunday, September 17, 2006
一個年份的心情
 過了一個月令人又愛又恨又胃痛的編輯生活,下周一終於可以暫時舒一口氣,到北京去,繼續未完的紀錄片拍攝工作。我的胃收到風聲,由星期六開始就變乖了,不再折騰我。
過了一個月令人又愛又恨又胃痛的編輯生活,下周一終於可以暫時舒一口氣,到北京去,繼續未完的紀錄片拍攝工作。我的胃收到風聲,由星期六開始就變乖了,不再折騰我。早陣子,有記者訪問魯迅後人,讓我突然想讀魯迅。翻出今年在政府舊書義賣中以五大元買入的《准風月談》,結果讀了好幾天,都不願放下。
《准風月談》編錄了魯迅1933年在上海《申報》以各種筆名撰寫「自由談」專欄的文字。說真的,魯迅的雜文雖然有名,但今天能看得懂的人不多,因為其雜文多是調侃時事和文壇怪現象,我們不活在那個時代、那個context之內,僅觀文字的表面意思是無法理解魯迅想說什麼的。
這其實也是專欄文字的一個特色,打個譬喻,幾十年後,如果有人看到2006年某專欄文章寫到「巴士阿叔」,相信也只能摸不著頭腦罷?
我讀的版本,是台灣「風雲時代」魯迅全集版,精彩之處在於它有非常詳盡的注釋和一些備考文章,有助消除「閱讀障礙」。一下子,1933年上海的光怪陸離事(如電車上的售票員不給乘客車票,名為「揩油水」;翻譯外國作品的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政府出售「航空公路建設獎券」,頭獎五十萬),都活現眼前。魯迅到底想窒什麼,也就一目了然。
書中收有幾篇文章,是調侃施蟄存的(因他推薦年輕人讀古文,認為傳統文化不能完全拋棄)。本書的編者為了令讀者看得明白,輯錄了施蟄存反駁魯迅的一些文章,兩人筆戰的脈絡因而分明。以前,對於魯迅這些敢於反對舊禮教、敢於指出中國人劣根性的知識分子,我是很敬重的;不過,也人長大了,對五四時期的歷史多一點了解,今天的我,對施蟄存這些在「反傳統」潮流如火如荼的時勢下,仍敢於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反而愈來愈敬重。如果我們今天真如魯迅等人所提倡的那樣,不讓學生接觸任何古文、詩詞和中國文化,那將是另一種模式的文革。
雖然我不很贊同魯迅對舊文化的立場,但無可否認,他的文字很精彩(如施蟄存所言,魯迅的古文底子很深厚,對他的寫作很有幫助)。但讀《准風月談》,不單單是讀魯迅令人捧腹又抵死的文字,也同時是在讀1933年歷史的細節,讀一個年份一些人的遭遇、心情。這當然比起讀一本臚列大史事件的狹義歷史書來得有血有肉,也更有「煙士披里純」(即是inspiration,魯迅語 ^_^)了!
Saturday, September 02, 2006
愛國者與間諜
『前日傳來程翔判監五年的消息後,這年來一直保持低調的程太劉敏儀終於打破沉默,除高調接受傳媒訪問外,前晚更公開程翔「給家人的話」,向全世界發布丈夫堅稱自己無辜的信息。 ...... 據知,劉敏儀的轉變,是因程翔被指從事間諜,對一向愛國的程氏夫婦造成很大打擊,因此即使程翔仍身在牢獄,家人都不惜冒險,高調反擊法院的指控。
有不少親北京人士向劉敏儀分析,程翔至今被扣押了十六個月,換言之只要再多待四個月,便可申請保外就醫,回港與家人團聚;若劉敏儀高調反擊,或觸怒北京,影響保外就醫機會。』
在香港,大部分人都明白,「愛國」這個詞,含有一種嘲諷的意味。除了因為回歸後有些人「突然愛國」之外,還因為「愛國」在今天是不入流的、老土的。而且,對於年輕一輩的人來說,要去愛這樣一個貪污是家常便菜、法律是些虛應文章的國家,確實有難度。我不知道其他同輩香港人有何想法,但「愛唔落手」,至少是我對這個國家的感覺。實在無法對她有一種極度投入的情感,頂多只有一種抽離、客觀的關懷,一種人人都有的、inborn追求公義的衝動。
但「愛國」是個歧義詞。當說程翔是個愛國者時,我們都明白,這個詞不含任何嘲諷、老土意味,「愛國」在這裡有另一種意思。是一種幾乎已經絕跡的完全投入的愛。是貨真價實的愛。是真切地希望國家變得更好(包括希望海峽兩岸的分裂局面可以結束,希望國家的法制可以更完善,等等)的愛。
很多人(譬如我媽)卻不知道有程翔這樣一種愛,反而認為聽(共產黨的)話就是愛國,愛黨等於愛國。這當然是犯了邏輯上的錯誤,因為政權和國家,不是兩個相等的概念。
但偏偏,當權者認為「愛國」是如此定義。
愛國者被當成間諜,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具侮辱成份了。
但願,程翔不會因為這次遭遇而後悔過去做過的事情。
但願,更多的聲音不會帶來反後果。
但願。
Sunday, August 27, 2006
農民下一代的課桌在哪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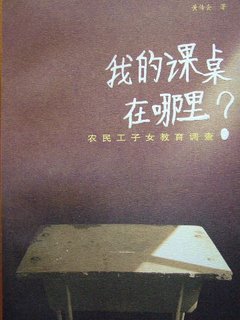 在北京海淀的風入松買了不少好書,其中《我的課桌在哪裡?》(黃傳會著,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我最喜歡的一本。
在北京海淀的風入松買了不少好書,其中《我的課桌在哪裡?》(黃傳會著,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我最喜歡的一本。 真不明白,為何香港賣大陸書的二樓書店,來來去去賣的都是一些無法令我提起意欲購買的書。也許因為大家都只是在深圳入貨?其實中國有很多好書我們都錯過了。如果我有錢辦一間大陸書書店,一定會入最精彩的貨色;馬國明老闆話齋:「無人買,咪自己要囉!」
近來喜歡讀一些和中國大陸國情有關的書籍。這本報告文學講的,正是北京數以十萬計農民工下一代(沒法受)教育的嚴重國情。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其中超過一億為流動人口。中國農村生活太苦,農民遠離家鄉跑到城市找工作,是為農民工。農民工的下一代,跟著父母來到城市,但因為沒有城市戶籍,無法在正統學校唸書。並不是說學校絕不取錄外省學生,但取錄的前題,是必須繳付幾千元的借讀費、贊助費。
中國各個省市的教育經費,是中央政府按該地登記戶籍的學童人頭比例而定下的,因此外地來的學生,便需自掏腰包付出本來該由政府付的費用。(所謂贊助費,意思也許是由學生自己贊助學校,來讓自己讀書?)十多年前,河南固始縣一名鄉村教師張保貴,見到在北京收廢品的同鄉竟無奈地將子女送回老家又舊又破的鄉村學校讀書,才知道原來農民工子女很多都無書讀。他因而興起到城市開辦農民工子女學校的念頭。於是,他在北京某廢品市場租了兩間小平房,招了十多個無書讀的孩子後,便正式辦起「學校」了......
張保貴之後,北京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如雨後春筍湧現,但大都非常簡陋。又因為有利可圖,部分學校純粹是為賺錢而開,令質素良莠不齊。可沒有這些非法辦的學校,很多農民的孩子們,可能到今天仍只能整天遊蕩、無所事事,繼承上一代的貧窮命運。因為中國當局對農民工子弟學校一直沒有清晰的政策(也難怪,始終這是新興事物),這些設備異常簡陋的所謂「學校」,不時被政府查封、取締(有些經過多番斡旋,終於取得辦學准許證),卻是農民子女脫貧的唯一希望;中國國情之荒誕,實在已超越了人的想像能力。
[有法不依是中國的特色。書中提到,北京市雖於零四年下發通知,對農民工子女免去借讀費、贊助費,但事實又是另一回事了。「中央針對農民工的政策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為什麼?關鍵是利益問題。」「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中央財政沒有下撥資金,造成輸出地和流入地政府都不願意管。」據零四年的一項官方統計,北京市流動兒童人口已超過31萬,其中21萬在公辦學校就讀,二萬在「有牌」的民辦學校就讀,八萬幾在「無牌」的民辦學校就讀,幾千名兒童未入校就讀。]
Friday, August 25, 2006
西潮(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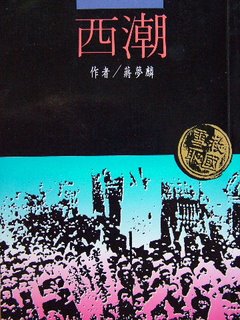 寫了上一篇blog後,才知道原來《西潮》並不是中學中文科的範文,而是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指定讀物之一。(謝謝思存指正)
寫了上一篇blog後,才知道原來《西潮》並不是中學中文科的範文,而是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指定讀物之一。(謝謝思存指正)在網上讀到,蔣夢麟(1886-1964)是在抗日戰爭時於西南躲警報時,在防空洞裡用英文撰寫《西潮》的。用英文撰寫,是因為防空洞光線不足,使用英文較易辨識。英文本1945年在美國出版,中文譯本則於12年後在中國發行。
我一直對上世紀初出現的中西學堂,很感興趣。1898年左右,蔣夢麟離開家鄉到紹興的中西學堂讀了兩年書。他有一段文字描寫當時學習的情況:「我在中西學堂裡首先學到的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是地圓學說。我一向認為地球是平的。後來先生又告訴我,閃電是陰電和陽電撞擊的結果,不是電神的鏡子裡發出來的閃光......過去為我們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個接一個溶化。」(59頁) 由死記硬背的私塾過渡到重研究推敲的西學,中間的cultural shock,大得會令人會精神分裂吧。
當日俄戰爭(爭奪中國東三省的控制權)打得激烈時(1904年),約20歲的蔣夢麟進了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預科,為到美留學作準備。蔣夢麟應是差不多最後一批曾考科舉(約18歲考中秀才)但最後選擇或被迫選擇西學的中國讀書人,而蔣是前者。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廢科舉。「廢科舉的詔書是(同年)日本戰勝帝俄所促成的。代替科舉的是抄襲自日本的一套新教育制度。」(84頁) 當時中國政府和中國人還未敵視日本,反而向她的制度學習,很有點雅量;不過1931年9.18事變後,日本卻鯨吞中國了......
Friday, August 18, 2006
西潮(一)
幾年前開始,愛上了清末民初的歷史。因中學唸理科,中史只唸到中三程度,對清末歷史的認識很皮毛,且大部分都是自修得來的,極無條理。譬如民國成立後,二、三十年代的軍閥割據情況,便不甚了了,而對袁世凱的歷史角色和功過,也沒有頭緒,看了唐德剛的晚清系列,才開始搞得清人物的關係。
今天大家都會說,並沒有一個所謂客觀的歷史,一切全取決於寫歷史的人的立場、身份。但以前讀中學時,當然不會想到這些啦(不知現在的學生會否聰明一點?)。現在回看,中學時的歷史課本,永遠採取一種中立和抽離的觀點(列出遠因近因年份日期影響),卻毫不立體(如果我只能以幾十字來寫六四事件的歷史,相信也一樣立體不來),連最震撼人心的歷史事件如五四,也成了枯燥的流水帳。
其實歷史全都是由有著七情六欲的人所作的活動,充滿偶然,充滿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我覺得民國建立時的最大偶然,是孫中山及時在革命人士準備成立參議院和選舉臨時總統時趕到(之前他在美國),於是冷手撿個熱煎堆,成了國父。蔣夢麟寫的晚清民初,最吸引我的地方,正是它的純粹個人觀點,絕對不會裝作中立(書的後部分很多時還反映了他作為大學領導人的觀點),而且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充滿「現場感」(當然,因為他就在現場嘛)。
我覺得,蔣這一代人,讀四書五經長大,考過科舉(中過秀才),然後轉到西式學堂,再到英美著名學府留學,完全有資格做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較」。(對某個異國文化的了解常是基於比較。總覺得,香港人因為不中不西,沒有堅實的中國文化傳統作參照點,因而對歐美文化的認識也難以深入。)蔣在書裡便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比較中西文化,有不少精到見解。
蔣夢麟對於軍閥時期的學生運動有不少著墨。令我有點不解的是,他以「囂張跋扈」來形容參與罷課示威的大學生。可能因為當時學生「拿學校當局作為鬥爭的對象」?這和魯迅的文章總是很同情學生,恰成對比。或者因為蔣夢麟是為國民政府工作的,而學生多受共產主義的思潮影響?
那時候,死亡應是很常見的事罷,蔣夢麟對一些人的死亡總是輕描淡寫。「段祺瑞執政的政府顯然認為機關槍是對付一切群眾行動的不二法門,因此在一群學生包圍政府時,他就老實不客氣下令用機關槍掃射......我在下午四點鐘趕到出事地點。......廣場上,男女學生傷亡枕藉......救護車來了以後,把所有留著一口氣的全部運走,最後留下二十多具死屍,仍舊躺在地上」。或許於亂世擔重任的人,已無暇對單個生命的結束感到難過。 (之一)
Wednesday, August 09, 2006
信報賣盤
很多年前在信報文化版當過小記者。直到現在,信報那種「手工業」運作方式(記者常要參與「睇版」,通常午夜 12 時才放工),和幾近「放任」的編採氣氛,仍然令我難忘,也非常懷念。雖然我並不完全贊同信報或林先生所持的右派自由主義思想,但卻很感激信報一直以來願意給出一整個版面來報道文化新聞。不像某些中產報紙,文化是為了點綴,為了附庸風雅。
李先生入主信報後,信報會變成什麼東西,現時沒法猜得到。只希望,不要變成一張市場導向的報紙就好了。
Sunday, August 06, 2006
雙城買票記
七月三十一號,由北京坐早班火車到開封。沒有想到一個「七朝古都」(戰國時的魏國、五代時期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北宋和金,皆建都於開封),今天竟落得如此破落收場。這裡幾乎沒有任何高於五層樓的大廈,店鋪都很破舊。街頭的電線桿亂糟糟的糾纒著。行人路常常是破損待修的模樣,崎嶇不平。空氣裡瀰漫著一層灰塵。一個經濟發展不佳、城市管理不善的地方。但最令人感覺怪異的是,一旦你走進旅遊景點(譬如清明上河園)時,會發現裡面是很乾淨整齊的,和外面好像是兩個世界。不過鼓樓夜市的小食的確多,灌湯包子也的確很美味。(可惜沒有去到阿Kit建議的「第一樓」......)
由開封坐了一百分鐘巴士去到鄭州,本來想留在鄭州一、兩天看博物館,可是抵逹時這城又是一個快要狂風大雨的模樣,遊興大減,遂立時到火車站買票回廣州。
在鄭州只停留了兩個小時左右,但是對她卻很有好感。那是因為,在鄭州買火車票竟出奇的順利。由排隊到買票,用了不到三分鐘,而人龍大約有十人。
在這之前幾天,當我還在北京時,曾到北京火車站買開往開封的硬臥舖車票。那天,售票廳的各條人龍不算太長,我暗自慶幸著,然後隨便挑了一條人龍排隊。排了大約十多分鐘,卻沒有見到任何人是成功買了票離開的。因為售票的窗口擠著一大堆人,根本沒法搞清是什麼回事,我只能繼續呆等。當前面也在呆等的人陸續放棄離隊之際,我向售票窗迫近,這才終於聽到隊頭的人說,這個窗原來已停止了辦公!大家於是一哄而散。這次我學精了,先在某窗口旁視察一下,肯定是有人辦公後,才去排第二次隊。
可是情況並不順利,第二條人龍同樣沒有吋進。我開始研究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其中一個問題,是窗口前實在擠著太多不打算買票的人,是他們令真正想買票者必得花很多氣力和時間才能擠到窗口前。而且因為隊的前端很亂,有一些人打尖,令隊伍的進度更慢。(後來又發現,因為售票的電腦不時會死機,也減慢了賣票的效率)
很明顯,那些擠在窗口前的人是黃牛黨。排隊時,也常有人走過來兜賣黃牛票,很多人因為不想浪費時間而幫襯。找出了問題,於是又去挑另一條人龍。這龍我已認真觀察過,發現賣票員的而且確在回答買票者的問題。
結果,我在這第三條龍排了大約二十分鐘後(前面約有十人),終於買到去開封的車票!回頭一看,我第一次排的那個「假隊」,又排了十多個人!他們註定又是白排了。
前前後後,我在北京花了約一個小時來買一張車票。我很想知道:這種痛苦的買票過程,是否不能避免的呢?當我來到鄭州的火車站,便發現原來北京站的問題,別人一早已解決了。在中國的火車站買票其實可以完全無痛。
鄭州是河南的省會,火車路線四通八達,因此買票的人絕對不少。但鄭州火車站的售票廳,有很簡單而有效的措施,來增加賣票的效率。首先,在售票窗口前,除了排隊的位置外,當局都加裝了鐵欄杆,任何人都不能企近窗口前。而在窗口的正前面,是一個像超級市場入口的旋轉門,因此每次只能有一個人經由旋轉門來到窗前買票,其他買票者都要乖乖的在後面排隊等候,不能打尖(因設有欄杆令其他人不能擠進隊)。就是如此簡單的設計,令我很輕鬆地在三分鐘內買到票!
不禁想,北京貴為首都,為何火車站的管理者反而沒有去處理黃牛黨和賣票超級緩慢的問題?一個省會火車站的管理者也想得出的解決方法,北京人沒理由想不到罷?
無法不認為,這是因為貪污而造成的結果。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但似乎也是最合乎「國情」的猜想罷。在北京生活的紀錄片主角跟我們說過,各項奧運建設的進度簡直不知所謂。主要原因,是原本主管奧運工程的北京副市長(劉志華),六月時因「生活腐化墮落」的罪名而落馬(真正罪名當然是貪污啦。他掌管的可是奧運會40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項目肥缺!),令高層亂作一團,完成各項工程是遙遙無期。
也許我是有點無限上綱,將買火車票的難和整個國家貪污問題扯在一起。但簡單如火車站的管理也做不好,不是太令人失望了嗎?見微知著,我覺得,首都的火車站,多少反映了這個城市的亂象。
Sunday, July 30, 2006
司馬台長城(北京之行四)
可是今天開始,又是令人無處可逃的熱氣!
昨天趁著還有一點雲蓋著大太陽,去了司馬台長城。雖然霧氣很大,但是感覺還真不錯。這個長城在一個小水庫旁的山上,被水庫分成兩邊。因為長城實在非常陡峭,所以只能很慢的爬。雖然聽說司馬台長城是最沒有人工修飾的長城,但看上去長城的磚都是新的,唯有一些烽火台/城樓保留著破落的外貌。最有趣是水庫/河的兩旁各立著烽火台,很有氣勢。可惜若要過河上的橋便要收費五元,令同車那位波蘭太太大為掃興。
明天便啟程到開封,北京之旅也暫時要結束了。
Thursday, July 27, 2006
單騎走京城(北京之行三)
我由位於大柵欄附近的四合院旅舍開始,先踏到前門,再去崇文門,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北京明城牆遺址公園。這是個新修建的公園,以前,城牆一帶是亂七八糟的店鋪和民居,北京政府在幾年前將這些店和人移走,又從北京市民處得回四十多萬塊城牆磗(就是說,市民以前都把磗取回家使用了),重新砌出城牆,並在城牆的旁邊植上樹林和草地,令古城牆終於像個樣。
現時,國內開始明白了「修舊如舊」的道理,不再白痴地用新的磗頭夾硬將城牆缺去的部分補上,或加上一些難看死的現代裝飾,這實在是很大的進步。古樸的城牆保留著殘缺,自有一份蒼涼。
下午踏單車去參觀後海恭王府花園。可是因為「和珅效應」(和珅曾於恭王府居住),花園裡擠滿了一團團的大陸旅行團,只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吵!這種旅遊經歷是最痛苦的了。由後海踏車回到旅舍,已經是五時,人累透了!
Sunday, July 23, 2006
北京動物園(北京之行二)
十年前來過這動物園,當時是很殘舊的。現在的動物園,美極了:地方廣濶、種滿大樹、動物的生活空間大了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開放式的,沒有鐵籠子。可是有兩個美中不足的地方,一是買票入場時人們都不排隊,亂擠一通的像暴民;二是仍然有人喜歡餵飼園裡的動物。我在動物園看到一張超巨型的剪報(十年前的),講述北京動物園有不少動物因為吃了遊人投入的塑膠袋而死掉,並呼籲北京人不要亂餵動物。看來現在北京市民已收歛了很多,又或者因為一些籠子已改成玻璃屋(譬如熊貓館),根本不能投食物給動物罷?
來到北京其實很高興,但每回見到北京人買東西/買票不排隊、坐地鐵總是不會讓車廂內乘客先出車、隨地「放飛劍」,等等,我就會很氣忿!不知到何年何月,中國人的文化修養,才會有長足的改善?經濟走得太快,無論是法制、交通、城市基本建設,和人的質素,根本都追不上。
早幾天,我坐出租車回大柵欄青年旅舍,跟司機聊天時問他:「北京經常堵車(塞車)嗎?」他答:「不是經常堵,是天天。」我又問:「那麼到了零八奧運,不是堵死了嗎?」他答:「不會。黨中央說一句不讓你(私家車)出來,就不堵了。」
差點沒笑死,但卻是帶無奈的笑。
Friday, July 21, 2006
北京行之一
今天送走了導演和攝影師,正式開始了我的北京隨心所欲之旅。之前一個星期,北京的天空都是烏烏的,看著叫人心煩,可今天不知是什麼原因(可能大風?),早上五時半起床時便已見到一碧如洗的晴空!
這次來北京其實是協助一位師兄(大地mark)拍紀錄片,講的是一個北京流浪歌手的故事。不過拍攝不是太順利,導演於是決定改短行程。我也因此而有了更長的假期,共十八天!
昨夜拍完了所有footage後,我們一行三人去了圓明園的單向街書店。真是個好地方!一條長長的走廊陳列了大量文史哲及藝術書籍,而且都是不錯的書。這書店還有分店在後海,明天正式開幕,我也許會去看看。
在大陸上網很麻煩,很慢,而且似乎看不到自己的博客?!希望可以順利將這些文字放上網。
Monday, July 03, 2006
孩子
Saturday, June 03, 2006
Thursday, June 01, 2006
Tuesday, May 23, 2006
圓滿結束

論文寫得不好,但很享受寫作的過程。其實自我同一性的問題,涉及範圍很廣,包括philosophy of mind、腦科學和認知科學 (cognitive science) 的最新發展、靈魂或 reincarnation 是否存在的爭議等。寫完這篇論文,覺得論文觸及的,只是蜻蜓點水罷了。
很喜歡哲學,但最美味的佳餚吃足兩年也會滯,所以現在最想做的,是暫時拋開哲學,拿起一本小說,輕鬆地啃!上圖是哲學課程的宣傳postcard。由中大哲學系的張燦輝教授攝,我覺得照片拍得很有意境。
Wednesday, April 26, 2006
活在當下(梅村體驗之二)
去禪修前,沒有聽過「梅村」這地方,後來在營裡買了一本小冊子看,才發現那是個美不勝地的好地方!梅村位於法國波爾多區,有梅子串串的梅樹、池塘、青草地、藍天、白雲,難怪個個禪師也臉色紅潤。如果我也居於如此美景,天天吸清新空氣,禪修與否可能都不打緊了。法印法師在營裡第三天就傷風了,可能不習慣香港的混濁空氣?
我入營的理由很簡單,只是想學習禪修的方法。我不像部分營友般,有甚麼不能疏解的生命困惑(這才發現自己也算是個沒有太多煩惱的人)。以前曾經常常問人生的意義,事事都提不起勁,但現在,更想善用每一天,做當務之急要做的事。
我一直都不是一個宗教感很強的人,也不鍾情spiritual experience。但我相信禪修可以令人有一種 peacefulness of mind。近來覺得自己少了以前那種閒心。譬如每本書都只看了一點,便因為別的事情而放下,好像總在追趕甚麼似的。又譬如總是心思思想check email,但其實可能才剛check過。可能因為現在正處於一種過渡性的生活,總有點未settled下來的不安定感罷。
四天的禪修生活,讓我將生活重新調教好。沒有甚麼比早起早睡、吃健康的食物(如精舍自己種的蕃茄、茄子、生菜)、做早操、禪修,和過有規律的生活更令人身心舒泰。入營前幾天,凌晨三時睡覺,早上十一時才起床,人很累,又有一大堆工作要趕,簡直是萎靡不振!出營後,努力維持早起和素食的生活,竟感到說不出的輕盈。
對我來說,禪修,不如說是給自己的身與心一個整頓的空間。
常提醒自己,「活在當下」。這禪宗精神,被一般人誤解,以為是「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是過一種不負責任的糜爛生活之意。但其實禪宗講的是「用心感受當下」。譬如不要讓這一刻的心思放在抱怨過去曾作過的錯誤決定,或擔憂著未發生的事情之上。這一刻如在吃飯,便要用心去感受飯的味道;你會發現它是很甘甜的;這一刻如在散步,就用心感受路上的清風和蛙鳴,多麼暢快怡人。譬如想讀一本書,便全心全意去讀它,忘記書櫃上還有幾百本書在等我!
行也是禪(梅村體驗)
又譬如說,「行禪」(walking meditation)。所謂行禪,就是觀察和專注於自己的呼吸,令呼吸和步伐協調、一致。可以有很多不同組合,譬如我可以一步吸一步呼;或每行一步便呼和吸一次;又或者可以行兩步才breath in一次,再行兩步又breath out一次……諸如此類。我得說,這是我最喜歡的環節。(可能因為我腰骨不好,坐禪時會背痛令我很難專注,所以不太喜歡坐禪罷。又可能是我坐唔定。)
每天十一時一刻,我們由精舍的大門出發,經一條短短的斜路走落荃灣麗城花園的大街。我們行得很慢。起初要兼顧步履和呼吸很難,但當進入狀態時,會渾然忘記了外界和自己,汗水由勃子沿著手臂流到指尖,也不察覺。全身都很舒暢,而太陽暖烘烘的,鳥語蟬聲不斷……行到精彩處,壓根兒不能讓這個步行的韻律停下。
不過最有趣的,還是當我們行到大街的時候。這附近有銀行、商場、學校、天橋、巴士站,還有一條很多車很嘈雜的雙行線馬路。我們這群人像slow motion般,由法印法師帶領著靜靜地、慢慢地、專注地走著,周圍的人則以normal pace在講電話、坐公車、帶孩子上學、聊天。這個情境太精彩。他們有些瞄了瞄我們兩眼,有些干脆當我們無到。
後來一次discussion時,年輕的法氣法師說了一番精彩的話──我們如果走到香港某熱鬧的地鐵站或商場來個walking meditation,那應該比高叫口號示威什麼的,來得還更震撼呢!(法師竟然想搞群眾運動?)我很同意呢。一大班人一起行禪,說不定可以令香港人反思:為何總不能慢下腳步?如果有機會,我真想試試這樣做,會帶來什麼有趣的後果。
Sunday, March 19, 2006
憶奇斯洛夫斯基
十年,彷彿只是一剎那的光景。十年裡,兜兜轉轉做過很多工作,也換了很多遍人生理想,對事情的看法,已經和十年前變了一個樣,但對於奇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卻依然鍾情。而且,此情只有增無減。
已忘記了是在哪一年首次碰上他。那時候,日子過得天昏地暗,因為大部分時間都是躲在大學裡那間冷氣很猛的A814放映室,或旁邊非常狹小的preview room裡,「煲」電影。我記得,那時曾多次重看《情誡》(A Short Film about Love),而每一次都會隨著戲裡的小郵務員Tomek,一起經歷著純真的心靈如何逐漸被殘酷的現實所毁,很刺痛的感覺。
我也記得自己曾到灣仔新華戲院看《兩生花》。當時,故事看得不太明白,但是布偶戲那一場,卻令我異常感動,一直看一直流淚。後來,讀到奇斯洛夫斯基的自傳《Kieslowski on Kieslowski》談這電影的段落,他如此寫道:
We had seen a fragment of a puppet show on tv which was fascinating...(the puppeteer) was Bruce Schwartz.
He wasn't working with puppets any more because he couldn't make a living out of them...What has this moronic world we live in come to? A man who's the best in the world in his profession can't make a living out of it, because this profession only consists of moving puppets. He had to give it up and now hangs paintings.
He had all the puppets we needed. He suggested a story with a butterfly in it, because he had a puppet butterfly...It was extremely moving... When we finished shooting, the children immediately surrounded him and I saw a happy man.
He came and suddenly rediscovered a past, a joy or happiness which he'd once had in the past and which he'd lost. With our film, it returned for a while. That's terribly important.(.pp. 180~182)
我很愛布偶,但沒見過有哪一齣電影把布偶拍得如此優美動人。然而奇斯洛夫斯基的話,卻比布偶更加感動我。當時的我常覺得,拍電影是累人的工作。青春不斷燃燒,只為了拍好一個個鏡頭,於是不期然問:到底是人重要還是電影重要?
奇斯洛夫斯基認為最重要的是令得布偶師重拾生命的熱情。畢竟人才最重要。這本自傳,是我人生的十本好書之一。他的文字(他是用英語回答訪問者的),有時比他的影像更感動我。
Wednesday, December 21, 2005
遊戲規則
剛過去的周日(18/12),參與了反世貿遊行。昨天朋友Simon在電郵上說,不明白為何人們要支持韓國農民,因為他們保護自己的市場,令到第三世界國家的農產品不能進入......世貿的議題涉及很多範疇,我未敢妄下斷語,我只相信,玩遊戲最緊要公平。歐美國家一方面不准第三世界國家補貼農民,並且設高關稅阻止他們的農產品進入歐美市場;另一方面,自己卻巨額補貼自己國內的棉花、奶牛等生產。這種雙重標準,何公平之有?試問歐洲農民的每隻奶牛,每天有二塊多美元的補貼,是否說得過去?如果買便宜橙和便宜手機的背後涉入這種種不公平貿易,我寧願多付一點了。
Monday, December 05, 2005
民主算式
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聲稱有25萬人參加了昨日的遊行,《明報》委託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系高級講師葉兆輝,以及衛星圖片分析專家李偉鵬統計遊行人數,前者估計有7.2萬人,後者估計約9.2萬人,警方則稱有6.3萬人。(摘自明報)
老實說,我不太相信主辦單位所說的數字(25萬)。以一非常粗略的方式來計算的話:遊行隊伍三時許出發,五時抵終點,即約兩小時人龍才「鋪滿」全條遊行路線。我們假設之後的人也是兩小時走畢全程.那麼由五時至七時止,另一堆遊行人士才會「鋪滿」全條路線。遊行於八時左右結束,七時至八時這一小時的遊行人士,應可鋪滿「半條」遊行路線。如果我們知道由維園到政府總部的遊行路面要由幾多人才可以「鋪滿」的話,那麼就可以粗略算出遊行人數,即:
鋪滿路面的人數 x 2.5 次 = 遊行總人數
這計法當然有很多漏洞,譬如鋪滿路面的人數視乎「人口密度」而可有很大變化,遊行早段的「人口密度」通常會很高,而後段則疏疏落落;又譬如遊行的速度於早段和後段也會有不同;但這計法至少可以對人數有一粗略的估算。
如果民陣的數字正確,即10萬人才可以鋪滿整條遊行路線。我認為,如果六條行車線全開的話,十萬人還可算是個合理的數字,但以昨天的情況來看,實在有誇大之嫌.....我不覺得數字很重要,但實在不喜歡任何人誇大其詞。
對於在香港爭取universal suffrage,我覺得是不用有任何思想掙扎的。但今年MA課的「儒家與現代生活」,授課老師以及課堂中所閱讀的文獻卻對「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有很多批評。這有點令我困擾,因此打算以此作為此課的期終論文題目,近來天天都在讀相關的文章。自由主義將人視為atomic self,令「個人主義」在社會上大行其道,確是有它的問題,但一向以來我的想法都是:代議政制式民主縱使有很多缺憾,可是比起其他政治制度,它卻已是最好的一個,因為「民主」差到極只是民粹主義,「衰極有個譜」,但其他政制差到極的話,卻會成為專制獨裁,世界各國的共產政權就是很好的示範.......
以下內容摘自in-media上馬家輝的文章(明報2005-11-29) ,正好講出了我的心聲:
普選之作為普世價值,真正意義在於跨越了時間和地域限度,任何一個敢於自稱開明理性的社會皆須以此作為最基礎的公民權利,若真有時間,它必然是now;若真有地域,它必然是here。不分年齡種族,普選應是一切的起點。是的,普選是普世價值,是現代社會經歷痛苦折騰而沉澱出來的一種文明結晶;普選是現代社會政治運作的唯一選項,不應被濃縮轉移為時間、年齡、年份的工具計算;普選是政治哲學的深層底蘊,並非經濟投資的回報計算。當巴黎、倫敦、東京、曼谷、首爾、台北、台中、高雄、台南……的市民都可以透過普選來決定誰來擔任自己政府的最高領導,並且不是到了昨天才有這項權利,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怎有面目奢談自己的優勢?香港人怎可能再甘於自縛?
Saturday, December 03, 2005
Sunday, October 09, 2005
陳年剪報
 馬家輝是我喜歡的學者/雜文家之一。他總是認真地寫,絕不欺場。看到今期《讀好書》那篇「馬家輝的書房」,其中一段提到他早年在東方日報寫專欄的舊事,我赫然記起書櫃裡藏有一些舊剪報,當中幾篇,正是馬家輝十多年前的「少作」。
馬家輝是我喜歡的學者/雜文家之一。他總是認真地寫,絕不欺場。看到今期《讀好書》那篇「馬家輝的書房」,其中一段提到他早年在東方日報寫專欄的舊事,我赫然記起書櫃裡藏有一些舊剪報,當中幾篇,正是馬家輝十多年前的「少作」。翻出來細讀,才發現寫得真是細致;也許少了今天的一份老練,但耐讀程度一定比今天報章上大部分副刊文章為高。除了歎息當年的東方日報竟有空間容納這種高水準的文化觀察之外,這些剪報也真勾起我不少回憶。
1991年,唸中六的我仍然是一舊飯團,對很多事情一知半解。因為89民運的刺激,那幾年囫圇吞棗地看了一些與中國歷史有關的書,印象最深的是戴厚英的傷痕文學《人啊,人!》。雖然隱隱然地想更深入地理解這個世界,但是日常的生活不外乎返學放學,聽人人在聽的流行曲,讀些所謂名著卻根本不明所以等等。一眨眼,已經脫離了「青年」行列,依然時不時像一舊飯,可幸的是,現在終於可以作一幾乎全職的學生,認真思索很多還未想通的問題。
馬家輝說,每次回台北,看到自己書架上的書,都會感到溫暖,因為他會記起自己年少時「心中有無限的問號,那時又有意志解開那些問號。」「不像現在無論有沒有問號,都會將問號擱在一旁」。有心無力,真是中年人的悲哀。可以做的,也唯有是盡力而為罷了。

我一直希望可以讀到馬家輝的雜文結集,但對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總是希望把事情做到最好,而寫書這回事卻是永遠沒有所謂最好的......唯有繼續引頸以待。
〔上圖:「世紀末啟示錄」專欄;左圖:「博士生日記」專欄。兩者皆刊於東方日報,時約為1991至1992年左右〕
Sunday, September 18, 2005
旁聽生的嘮叨
經過一輪挑選後,上課時間表總算安頓好,而這兩周,除了本科的課外,旁聽得較多的是政政系,先後聽了蔡子強、關信基、馬樹人和周保松的課。作為一個旁聽/旁觀者,這些本科生的課給了我一些很奇異/詫異的感覺。讓我感到最詫異的,是我發現今天大部分大學老師,似乎已不敢對大學生有所要求,對學生的懶散已到了非常「容忍」的地步。蔡子強在第一堂課便開宗明義說,這個課要求很簡單,不用寫論文,考試都只是short questions,背背書就識得答;說的時候,蔡的語氣既帶點單單打打,又像無限悲涼似的。
如果老師們在課堂上不再對學生有適度的期望,學生們上課也不再有追求知識的熱誠,大家純粹是在虛應故事的話,則今天的大學教育,可說已經完蛋了。香港大學生欠缺主動性,對自己沒有要求,專挑容易過骨的課來上,彷彿已成事實;但我總覺得「牛唔飲水唔噤得牛頭低」,試問如果學校或老師「企硬」,學生們縱然想偷懶、蒙混過關,也根本沒有這個機會。但今天大學教授對學生的態度是「買佢地怕」,毫無執著,甘願作出任何讓步。上樑不正,下樑豈有不歪之理?
可幸的是,尚有擇善固執者(又或者,是尚有位高權重的有心人)。上星期一首次旁聽關信基教授的「Fundamentals of Government」。課上,關教授問同學有否按他上一堂的要求,讀三篇短文和寫下要點。廿多人的班房裡立時鴉雀無聲,最後只有一個男孩舉手表示有做預備。我作為一個outsider,尚且覺得場面尷尬,真不知道那些undergrad學生們心裡作何感想。不過作為系主任的關教授,並沒有顯得不悅(甚至還笑咪咪的)。但他也沒有就此放過大家:他要求同學們即時在堂上閱讀那些文章,然後分組作討論。心裡由衷的為關教授那一點點執著而感動。
以上是第一奇。尚有第二奇。我每逢周一下午會旁聽蔡子強,下課後則一個箭步由聯合跑落崇基(十五分鐘時間連買晚餐),旁聽李歐梵的文化研究課。這個極速由一個學科跳到另一學科的過程,令我忽然醒覺到,原來本科課程對一個人的「思維格局」的塑造,實在是舉足輕重。
從政政系的課程結構可以發現,政政系關注的是國家/城市的運作、行政這種務實層面的問題,但對於一個城市裡到底呈現怎樣的文化這種務虛層面的問題,此系卻是不屑一顧的。譬如,迪士尼這種美式文化,在大嶼山橫空出世後,對香港人的思維模式會有壞影響嗎?「刺激=歡樂」、「卡通人物的假笑臉=世界充滿真歡樂」,這些偏頗、inauthentic的價值觀,會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嗎?這些問題,其實理應是一個城市政策的制訂者所應關心的,可是在香港,它們往往只是沒有政治權力的文化評論學者所感興趣的議題而已。
讀新一期中大校友,說到政政系畢業生當上政府AO的是各系之冠。由是有點明白,為何香港政府官員們在規劃這個城市的時候,從來只會從經濟角度作考慮,而文化永遠無位企。
(地球之友的吳方笑薇早前在港台節目中說了一句我很認同的話:為何我們要為了一個假的樂園,而放棄一個真實的、美麗的海灣?這正是我討厭迪士尼的主要原因。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大家都喜歡「假嘢」?穿著卡通服的工作人員熱到死,為何大家覺得佢地好cute好過癮,爭著跟他們拍照?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有關迪士尼的種種,可參考地球之友和獵奇行動的網站。)
Wednesday, August 03, 2005
和活佛看七劍
活佛穿著喇嘛服,有點令人肅然起敬,但其實他比我還小幾歲,對很多事物都很好奇,有時又不大理會我們兩個女子談什麼,只顧看我帶來的雜誌(因為上面有一篇關於他們的訪問稿),倒很像個沉醉在自己世界裡的小孩子。活佛又給我看他剛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全新的仍未有蓋過印)。有趣的是,護照上姓氏一欄填上了「尼瑪」,而「名字」一欄卻填上了「XXX」。有姓無名,過海關時自然引起很多麻煩,但原來這還不是真相:「尼瑪」其實是他的「名」而非「姓」(因藏族人只有名沒有姓)。護照上沒有照實填報,實在是迫不得已,以免去更多麻煩,因為相信世界各國的海關人員,都難以接受一個人竟然沒有姓氏。有些事情我們是太習以為常,沒有留意它們其實是一種文化偏見。
晚上,帶他們去看徐克的新片《七劍》,比想像中好看。最令我深思的是:在故事中,皇帝下了「禁武令」,但是由始至終,人人都打個不停,「武」從未有真地被消除,反而愈禁愈烈,愈說沒有就愈有!這真是最最荒謬、諷刺之事。離開電影院,與我的台灣朋友講起這個想法,她說這讓她想起這次到中國大陸期間,看到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在節目裡說,中國是最反對法西斯的國家。可是她想,中國不正正是最法西斯的國家嗎......
我們在香港,可能已太習慣大陸的一套做法,習以為常,認為「唔係咁做的話就唔係共產黨啦」,但朋友作為台灣人,對大陸明目張膽禁制資訊自由的事情大感驚嚇:譬如她在四川某些省份的網吧上網時,便發現所有網址的字尾若是 tw 的話,網頁都一律被刪除,甚至,她連hotmail 和 gmail 也無法連上......
若果有一天,在中國大陸可以「自由」地連上地球上任何一個網站的話,我相信那就是民主真正在這個國家出現之時了。
Monday, July 25, 2005
盲眼手錶匠七(及李天命)
除了佛教之外,大部分宗教都認為宇宙是由「神」所創造。在這裡不談聖經或其他宗教經典內說過什麼(實在我也沒有認真讀過這些經典),只是想以邏輯去檢查一下:在沒有宗教經驗(如親眼見過奇蹟)的支持下,「神存在」的論證,邏輯上是否成立?立論是否有矛盾之處?
現今有兩個最為神學家所採用的神存在的論證,包括手錶論證(之前已提過)和第一因論證。以「第一因論證」來證明神存在,早已被哲學家批評得體無完膚,證明是一邏輯上完全站不住腳的論證,奇怪的是,很多傳教人士仍以此作為神存在的理性根據。至於手錶論證,今天則以「智慧設計論」的包裝重新在美國大行其道,但其中最根本的邏輯謬誤,與第一因論證又有點相似。李天命在新書中對此二論證批評得言簡意賅,讓我抄寫如下:
頁40:鐘錶論證,廢
...這個論證假定了精巧的東西必有製造者或創造者,但這麼一來,由於上帝該比人類更精巧,那麼必定有個超上帝創造上帝出來了?進一步又必定有個超超上帝創造超上帝.....?
首因論證,廢
「由於所有存在者都有其原因,因此有個存在者是所有存在者的原因-第一因-這個第一因就是上帝」
批:...如果說,所有存在者都有其原因,上帝是存在者,但上帝沒有原因,那麼這個說法就自相矛盾,因為這說法蘊涵著:所有存在者都有其原因而且並非所有存在者都有其原因。
手錶論證的謬誤較易理解,首因論證則可以再說一下。
每當我們認真的去追溯任何一件事件的原因時,便不能避免出現無窮後退的困局。而越往上溯,我們便越無法作出肯定的回答。世界是如何由無變成有的呢?在無窮的後退中,我們總本能地希望可迫近一個根源點,以結束我們的追問。
於是有人會以「神」來結束這種無窮後退的困局,並以「第一因論證」作為神存在的理由──即認為凡事必有因,並以「神」作為宇宙世界的終極因/自因,來結束無窮後退所造成的窘迫。即
「第一因論證」在邏輯上永遠都是自相矛盾的。在李天命的思方學中,這應被歸入「不一致的謬誤」的欄目下。但這個有謬誤的論證之所以會「長存不朽」,繼續被傳教人士亂用,又是什麼原因呢?這也許才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有一天我讀穆勒的自傳,讀到這樣一句:『我父親告訴我,「我是誰創造的」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因為這問題牽連到進一步的問題,即「上帝是誰創造的?」。』這句話使我猛然悟出第一因論證的謬誤。假如萬事萬物都必須有因,那麼上帝也必須有因,假如無因事物有存在的可能,則世界和上帝都可以無因,所以第一因論證完全無效……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世界的出現非有原因不可......萬事萬物都必須有開端的想法,實在是由於想像力貧乏所致。
我們無可避免地以為a事件的出現的原因,是較早前出現的一個/一些事件導致的,這些事件是a出現的充分條件,它們在時間上先於a出現。
但設若時間消失了呢?譬如,科學家認為時間是在大爆炸 (the big bang) 發生的一刻開始的。也就是說,大爆炸前沒有時間。我們知道,「因-果關係」只存在於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之內,沒有時間,則沒有因果,那麼唯有在大爆炸的那一刻開始,才有所謂因果,或者換個角度,可以說大爆炸一刻是宇宙出現的第一因。至此,我們已不能再上溯,因為「時間」還未開始呢。如果我們硬是要安插一個「神」作為第一因,反而顯得奇怪,因為我們無法知道「神」(若存在)所經歷的,是否跟我們相同的時間模式,即「過去-現在-將來」逐一顯現的模式。 因為只有在這種模式下的存有,才和因-果拉得上關係。
Monday, July 18, 2005
盲眼手錶匠六
無論進化論是否能解釋生命之源,我都傾向認同,地球上複雜的生物是由簡單的生物進化而來的。有些人會覺得進化論中的偶然性令一切變成不必然,但我卻覺得這種偶然性很美。
以往曾看過一些有關進化論的入門書,並不特別覺impressive,但幾年前有一本書曾強力地令我對進化論改觀。那是一本名為《Next of Kin:My conservations with chimpanzees》的書,講的是一位名叫Roger Fouts的生物學家,如何訓練一隻名為Washoe的黑猩猩以手語和人「交談」,並與她產生了微妙感情的故事。這書極度好看(尤其因為黑猩猩是我很喜歡的動物!),也談了一些進化論的branching概念。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指出,黑猩猩之所以沒有如人類般發展出複雜的語言,絕非因為牠們欠缺了理解語言的能力或intellegence,只是因為牠們的聲帶並不宜於發出聲音(所以做手語就沒有問題)。
我們常認為,人類和動物是截然不同的,因為只有人是有智慧的,而這「智慧」可以從以下例子中看到:只有人能創製工具,只有人能發展語言系統、文字、文化等......但今天,很多動物學家已指出動物也能創製工具,而Washoe的例子,更表明黑猩猩也有發展語言系統的能力......那麼所謂「智慧」,到底還是否真的是人所獨有的呢?抑或動物也擁有一點呢?如果人和動物的智慧呈現著這麼一種漸進性變化,那麼進化論看來是個頗合理的解釋物種多樣性的理論吧?
有些人討厭「進化論」,因為覺得它把人類生命的聖神和尊貴一下子掃走,同時更令所有的道德標準變成隨時可以揚棄的relative values。但我的看法正正相反。
若果進化論是真的,那麼生命的出現只有微乎其微的機會率;那麼人由一種動物本能式的存在,漸漸進展至有「自我」意識,再而進展至能將事物抽象化變成「概念」,三而進展至有語言、文字,一步一步,更而累積起知識、文化......這將是更為微乎其微、近乎不可能發生的事!若果在如此微乎其微的偶然中,人竟還能越出自我的牢籠,思索人之異於禽獸的地方,並發展出一套道德的理想,那麼這整個過程,不是比「神創造人」更讓人驚嘆不已嗎?更令人珍惜生命的得來不易嗎?就好像我中了六合彩頭奬,會覺得驚嘆不已、興奮莫名一樣,也會非常珍惜一樣。
我喜歡看樹看山看海看大自然和昆蟲動物,因為我覺得它們是如此精緻、美麗。而若果進化論是真的話,那它們的出現於世上,就更叫我拍案叫絕吧?
Sunday, July 10, 2005
盲眼手錶匠五
Experiments conducted to resemble conditions on primitive Earth have resul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ome of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proteins, DNA and RNA. …Scientists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building blocks of life” c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early in Earth history…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ether life could have originated by chemical processes involving nonbiological components. The question instead has become which of many pathways might have been followed to produce the first cells…
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原來科學家對這個問題已有共識?但我知道,只要我到大學圖書館關於進化論的一欄走一轉,就會找到很多反對進化論的書籍,而它們所說的正好與上面的引文相反:純粹的chance不可能觸發生命由死物中開展。其所引用的原因,一般會近似下段的內容:
The biochemical basis of complex life could not have developed through gradual evolutionary change because too many dependent variables would have had to have been altered simultaneously. [引自《Darwin's Black Box》一書的網上介紹]
換言之,仍然是complex design與chance的對陣!
來到這個地步,好像很一籌莫展,因為對於生物科技的知識,我只有幼兒園水平,而一個幼兒園生是沒資格對研究院的深邃理論作出品評的……
可以說的是,關於生命之源的問題,涉及了最新的科學發展,也涉及人們對整個宇宙之存在理由的基本信念。科學的部分實在無能為力,那麼不如轉個角度,以理性來驗視一下一些基本信念罷。[之五]
Friday, July 08, 2005
盲眼手錶匠四
問題一與二多少都是關乎化石證據的問題。綜合我看了的一些資料,科學家一般認為,有愈來愈多證據支持進化論。當中或存在一些具爭議性的地方,但最低限度,直至目前為止,地底的化石層次序是支持進化論的講法的:兩棲類化石不會在魚類化石下面,哺育類化石不會在爬虫類化石下面--這與進化論所提出的物種出現先後次序吻合:即是魚、兩棲類、爬虫類、哺育類、靈長類、最後是人...... 〔有關支持進化論的其他一些證據,可參考這本書中,「Evidence Supporting Biological Evolution」一章,網上可看全文。這是非常精簡的一本書,由美國一群頂尖科學家/進化論學者撰寫的進化論普及讀物〕
關於新物種是如何出現的問題,進化論其中一個學派「Punctuated Equilibria」(主將包括著名學者Stephen Jay Gould)提出了很合理的解釋。其所描繪的新物種進化圖像是這樣的:
當某一物種因為地理環境而分隔於兩地時,兩群生物會因為環境的不同、突變的不同以及「天擇」的影響,而出現很多不相同的身體特徵,最後,兩地生物因為差異太大而成為兩種無法互相交配的生物,新物種逐產生(所謂「新物種」的定義,就是一種不能與已有物種交配的物種);稍後,此新物種因各種理由去到「舊物種」生活之地,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兩物種會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況,沒有任何進化發生。
「Punctuated Equilibria」的講法,其實可以說是學者們按著已知的化石證據而構想出來的理論假設。長久以來,已發掘的生物化石顯示,新物種是突如其來地出現的,新舊之間,沒有舊物種漸漸過渡到新物種的化石證據。在達爾文的時代,這是個很棘手的問題,一般是以「化石資料未夠多未夠全面」來作為解釋,而「Punctuated Equilibria」就是嘗試化解這個化石之謎:已發掘的化石中找不到物種在「進化中」的證據,因為物種是在另個地方進化的!就算我們在發生進化的地方進行化石發掘,也會因為進化的時間很短促,而大大減低了「進化中的動物」變作化石的機會。
對於化石證據的問題,我自問是門外漢,也不知道最新的發展是如何,因此無法評價。現在且來談第三個問題,即生命之源的問題。
「地球上第一個生命體,不可能是偶然由非有機物質產生的」,是創造論者最常高舉的反對進化論理由。對此,Richard Dawkins特別闢出一章來回應。
Dawkins是以機會率來回應這個問題的:這種偶然性是有可能的,因為其所涉及的時限是如此之長:
The fossil history of earth suggests that we have about a billion years to play with, for this is roughly the time that elapsed between the origin of the Earth and the era of the first fossil organisms.
即是說,由地球開始形成(約45億年前)到首件生命體在地球出現(最古老的有生命化石是屬於35億年前的),之間相差了10億年〔這令我想到李嘉誠捐給港大醫學院的十億。將十億元換成十億個一元大餅,然後每年使用一個,是就我用來visualize「十億年」的方法〕,因此由死物變出生命這一過程,足足有十億年的光陰可供差遣/玩弄。而Dawkins認為十億年是「夠用有餘」的。
第一個生命的出現,到底算不算是個奇蹟?還是一種「超級好運氣」呢?有時我會覺得,在十億年裡的確什麼也有可能發生;但有時我又會懷疑,非有機物質真的可能變成有複製能力的「生命」嗎? 至於Dawkins所採的態度,和哲學家休謨所採的是一致的,就是否定「奇蹟」:
Events that we commonly call miracles are not super natural, but are part of a spectrum of more-or-less improbable natural events. A miracle is a tremendous stroke of luck.
奇蹟?運氣?我贊同「進化論」的最基本原理,即「天擇」加「突變」可以令物種進化及令新物種產生,因為cumulative selection的效力的確驚人。但若回溯到「物種進化」最初始階段時,cumulative selection還未有機會出場,生命體的首度出現只能靠純粹的「運氣」……我是傾向認為很多所謂奇蹟只是彩數。但生命出現也只是彩數?這個結論卻令人不安。
但不安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漸漸發現,這種不安感的浮現,並非因為我們覺得「死物爆出生命」的機會率超細(因為如何細也都總有可能),而是因為我們在情感上難以相信,一種理應是神聖的東西,其來源竟是如此不神聖,如此不必然,如此「其求」,如此「咁啱得咁橋」……!生命之美/之充滿著智慧的設計,難道不應該deserve更高尚的來源嗎?
至此,相信我們已來到了創造論和進化論爭拗的根源點,也即是又回到Design Argument了!反對進化論的,認為Life deserve more than chance。同意進化論的反駁:Why not?
現在我仍想追問的是:為何人會本能地認為生命是神聖的呢?
愚見認為,那是因為生命當中,存在一仍未能被解釋清楚之物,令我們感到生命不可能僅是物質的演化。此物隨著生命而來,又隨著生命而逝;它令我們知道有我和他人之別,知道過去我的生命本不存在,未來我的生命會有盡期。它令我們無法只是單純的按動物本能過吃睡繁衍的生活,而必得尋找存在的目的,必得問我是誰?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我所指的,是「意識」、「自我」。是一種能抽離於自我然後對自我作出思索的奇妙能力。
「進化論」最令人無法接受的地方原來是它的潛台詞:「我」的存在只是「咁啱得咁橋」,「我」的來到這世界和消失於這世界原來是「無解」的,一切實屬巧合……
但也許生命就是如此的一種因緣際會,也說不定?我們暫且放開不安感,也暫且不上溯至宇宙的起源的問題(容後再談),先來看看生命是由「死物爆出來」的假設,是否有科學證據支持(畢竟人類有時對自己有太高的評價)。〔之四〕
Thursday, July 07, 2005
盲眼手錶匠三
我常覺得,創造論者若因某一事與聖經的內容相衝突,而不願意去理解它的話,甚至無論反方提出任何理據都必定指責反方是錯的話,那他豈不成了一個盲從、迷信的人?聖經經過大量的翻譯再翻譯,歷經的時間又這麼長,當中因各地文化差異而出現的誤譯/不能譯/錯誤理解的情況,一定多不勝數。〔就我所知,所謂童貞瑪利亞也是個誤譯〕我作為一個沒宗教信仰的人,實在無法同意聖經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說了一大堆題外話和嚕囌,且回正題。
《盲眼手錶匠》一書裡所提到的Culmulative selection概念,很大程度解決了困擾進化論的其中一個爭議,即Complex Design的問題。但是,反對進化論者仍然會覺得,無法接受物種由無眼進化到半隻眼,由半隻眼進化到一隻眼。譬如書中引述了某典型反進化論的說法:
If the cornea is fuzzy, or the pupil fails to dilate, or the lens becomes opaque, or the focussing goes wrong, then a recognizable image is not formed. The eye either functions as a whole, or not at all. So how did it come to evolve by slow, steady, infinitesimally small Darwinian improvements? Is it really pausible that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lucky chance mutations happened coincidentally so that the lens and the retina, which cannot work without each other, evolved in synchrony?
這段說話又一次錯誤地將進化論等同了lucky chance mutations。不過,它也同時點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某些器官看來太渾然天成了(譬如眼睛或鳥的翅膀),如果器官是進化而成的話,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半隻眼或半隻翅如何可能!
但是否真的如此難以想像呢?Richard Dawkiins以眼這例子作反駁,指出晶體和視網膜不一定是雙生兒。一個生物如果沒有晶體,只有一個如pinhole camera般的器官,牠看到的影像質素也許很差,但無論如何牠都會比一個完全盲的生物有更大的生存機會。而如果在漫長的歲月裡,剛好因為基因突變而令一丁點透明的東西生在pinhole上,令影像變得較為清晰的話,則在「天擇」原則之下,這丁點東西將很可能進化成晶體,然後慢慢進化成「渾然天成」的眼睛。至於其他器官的進化,也是同樣道理。
Cumulative selection為各種生物的complex design提出了一個科學的解釋,但進化論仍有幾個具爭議性的問題:
第一,現時發掘到的化石,是否支持以上「漸進式進化」的講法呢?譬如化石學家有否找到一些眼睛末進化完的生物化石?或翅膀未完全成型的物種?
第二,一個物種會不斷改良,似乎不難接受;但到底一個物種是如何變成另一個物種的呢?又是否有化石的證據支持?
第三,就算我們同意物種是由進化而來,可是生物進化過程的第一步到底是如何出現的呢?換句話:地球上的第一個生命體是如何出現的呢?因為進化論裡不存在一個創造者,第一步的出現只能是一個純粹的偶然,也就是說,非有機元素的偶然聚合,竟能產生可以複製自己的細胞!這個「偶然」是否太令人難以致信呢?〔之三〕
Tuesday, July 05, 2005
盲眼手錶匠二
對Design Argument有少許認識的人都會知道,十八世紀神學家William Paley曾提出最為著名/最有影響力的Design Argument,即「手錶理論」:如果我們在海邊拾到一隻手錶,其精密的結構和各部件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將令我們不得不同意,這隻錶是有一個設計者的,其存在是有目的性的。同理,因為人的眼睛的精密程度,絕對不亞於手錶,因此可以推論,包括人眼在內的整個自然生物界,都是有一個設計者的。
而所謂盲眼手錶匠,正是Richard Dawkins對手錶理論開的一個玩笑:一個手錶匠在造手錶時,早已知道所造之物的作用/purpose是什麼(也就是說:本質先於存在);但如果我們認同進化論的話,所謂「大自然匠」就只能是那"blind, unconscious, automatic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它並沒有vision或foresight或purpose或mind,因此我們極其量只能稱它為「盲眼的手錶匠」!
Richard Dawkins寫這本書的目的,正是要說服讀者,我們單憑進化論,已能夠解釋自然生物的complex design,而無需抬出神或創造論來作解釋。我仍未看完全書,但是對作者在首章所說的一番話非常贊同:人們若不懂量子理論或相對論的話,是不會隨意去反對它們的;可是當面對的是進化論時,則無論人們的認識是多麼淺薄,他們都會大模施樣的去反對它!這怎不令人嘖嘖稱奇!〔其實我正正是在早陣子遇上這種奇事,因此才產生一種「鋤強扶弱」的心態,開始去找進化論的書來看〕
Richard Dawkins指出一般人對進化論的最大誤解,是以為進化論講的僅僅是一種偶然性、隨機性(chance and randomness)的機制,因此對進化論的主要攻訐通常是:自然世界裡充滿了像眼睛這種有著complex design和結構的東西,它們根本不可能僅僅因偶然的基因突變(mutation)而產生出來,因為有complex design之物偶然被產生出來的機會率只是若干億份之一!
的確,沒有人(無論他是否贊同進化論)會相信一隻有著精確對焦能力的眼睛,會是在單一次的基因突變中由一團細胞變出來的。事實上,由無眼到有眼是經過億萬代偶然的突變。雖然如此,「偶然性」卻並不是進化論中最重要的成分,必然性才是呢:"Chance is a minor ingredient in the Darwinian recip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ngredient is cumulative selection which is quintessentially non random"。
要了解cumulative selection ,便先要了解natural selection。Natural selection即是達爾文提出的所謂「天擇」,其意思是:若果某一個生物因為偶然的基因突變,而令牠比其他沒有突變的同類較能適應環境(譬如牠的腳靈活一點,或毛色與周圍的樹林接近一點...),則牠便有更大的生存和繁殖機會。漸漸地,而較不能適應環境的同類將被淘汰掉(因為大自然的資源是有限的)。這種淘汰制,絕不是以抽籤形式進行的「隨機式」淘汰制,而是據生物適應環境的能力之多寡來作決定的,因此「天擇」與基因突變不同,它絕不是講chance的。
其實我們多少都經歷過「物種的進化」:如感冒菌經常變種,殺虫水漸漸殺不死曱甴等。而且,人類其實一直都在利用物種會突變的這種特質,來迫使物種朝人類所希望的方向「進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人類對各種花卉和谷物進行品種改良,令它們更符合我們的需要;另一例子是,在一萬多年前,人類將狼繁殖成不同品種的狗隻。所謂人工繁殖,其實就是讓人擇/artificial selection(人的判斷)取代天擇罷。
說回cumulative selection。絕大多數進化論學者都同意,每一次的「基因突變」其實都很微細(即所謂漸進式的進化論學說),而所謂cumulative selection,正是指這些微細的改變,會一直積累給後代。滴水成海洋,過了幾千幾萬代之後,其改變將顯得很巨大。在基因突變(偶然的變數)和天擇(自然界必然會淘汰適應力較差的生物)的相輔相乘之下,就算是一些如眼睛般非常複雜的東西,也有可能由簡而繁的進化出來。
為了解釋cumulative selection,作者寫了一個名為Blind Watchmaker的電腦程式,來模擬物種的進化。程式裡,有九個可變化的基因,負責控制一個樹狀圖案的各個變項(如每條樹枝的長度、樹丫的角度等)。樹狀圖案每「繁殖」一次便會有十八個「後代」,每個後代都有一個基因與其母樹不同(可能是加一級或減一級的改變),因此它們與母樹圖案都有點不同。玩這個程式的人,要從這些後代中選出一個樣子最像動物的後代,然後用這個後代再繁殖下一代,並在這些下一代中選出一個最像動物的來繁殖後代......,如此類推。有趣的是,大約過了廿九代,繁殖出來的圖案已相當像動物,跟原初的樹狀圖案大相逕庭。
其實這個電腦程式是個極度壓縮的模擬進化過程,因為在現實世界裡,基因突變並不出現得如此頻繁。但此程式很清楚的解釋了cumulative selection的巨大威力。〔之二〕
Monday, June 27, 2005
盲眼手錶匠一
“This textbook contains material on evolution. Evolution is a theory, not a fact,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living things. This material should be approached with an open mind, studied carefully, and critically considered.”
六名家長因不滿當地教育部這做法有違政教分離的原則而告上法庭,獲勝訴,但政府方面已打算上訴,事件最終如何發展仍是未知數。(新聞來源:http://msnbc.msn.com/id/7963494)
這則新聞令人嘆為觀止。若本於公平原則,此縣政府是否應在所有聖經上也貼上sticker,表明「創造論是一個論理而已,this material should be approached with an open mind, studied carefully, and critically considered」?可惜,美國佬做事從來不公平,只有佢講無其他人講。
Friday, June 24, 2005
倫敦、諾曼第
至於在法國諾曼第,我們在陶老師朋友的別墅裡,老實不客氣的住了三日兩夜。諾曼第的海和天和懸崖,美得沒話好說,請自己看照片好了。陶老師這位朋友是位畫家,也是食家,為我們煮了多頓美味的菜餚,包括雞和鵝肝。其實想到那些鵝天天被灌食,心裡真不好受,但主人特別為我們而買的菜(他自己高膽固醇不能吃),又不能不吃。其實我最愛的還是那些用炭燒古法烤的法國長麵包Baguette。配上農民手打的咸牛油,真是世上最美味的東西。至少我這個麵包癡如此認為!(這次旅程沒有帶相機,以上照片都是陶老師拍的。)
Monday, April 25, 2005
心靈哲學
有個學者講過,一個時代流行什麼東西,那東西準會被用來比喻作人的心靈。上世紀末最流行的當然是電腦,因此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大行其道,人的 mind 被哲學家/科學家視為只是一個電腦軟件,給它 input,它便給你 output。Mental state 只不過是將感觀 input 轉化為行為 output 的一台機器,沒有什麼神秘性。功能主義者甚至不關心這個「軟件」內的構成是什麼,換句話:不理黑貓白貓,捉到老鼠的就是「貓」(那管它可能是機械貓)!
我對功能主義完全不能苟同,因為功能主義無法解釋qualia的存在。Qualia這個怪字,意指人的意識所直接感受到的種種感覺,如看見紅色時那「紅」的感覺、痛的感覺、生氣的感覺、嗅到花香的感覺、墮入愛河的感覺......總之就是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東西。如果人的意識純粹像所有「人造物」般只為完成一些實際的功用(如鎚子有鎚東西的功用、筆有寫字的功用),那麼為何還要有 qualia 存在?不如人就像電腦般沒無知無覺算了。
功能主義對意識裡最重要的一環(subjectivity and private access of mental states)視若無睹,實在令人非常震驚。我又想,本世紀不知又會最流行什麼呢?哲學家又會繼續想到用什麼來類比人的心靈呢?只希望不會流行複製人,否則人的心靈的獨一無二性可能也會受到質疑哩。
Sunday, April 17, 2005
仍然有夢
是為此blog的序。












 西湖邊的「知足長樂」。好字,好句!
西湖邊的「知足長樂」。好字,好句! 





 巴黎歌劇院
巴黎歌劇院 
